(报告出品方/作者:中银证券,张晓娇、朱启兵)
1 十年之间生育率的变化
自 2016 年之后,我国新生儿人数逐年快速下降,2021 年我国新生儿人数勉强维持在 1000 万人上方。 新生儿人数受到与育龄妇女和生育率相关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不同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人数,以及 一孩、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生育率等。
生育率走势要细看
生育率走势分化,首先体现在 2015 年时点前后。先是 2015 年之后,生育政策经历过两次调整: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在全国 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 年 5 月,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受到 2015 年之后两次生育政策调 整的正向推动,生育率自 2016 年整体开始回升,从 2015 年的 30.93‰回升至 2016 年的 36.17‰,并在 2017 年达到近十年的高点 47.03‰后,维持在高于 2015 年之前的整体水平上。
其次体现在一孩和二孩以上生育率差异。一孩生育率整体依然维持下行趋势。2010 年-2014 年,生育 率整体维持在 20‰之上波动,2015 年降至 16.43‰的低点之后,2016 年虽然有所上升,但基本没有再 回到 20‰上方。生育政策的两次调整没有改变一孩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了二孩和三孩及 以上生育率水平上升方面。最明显的是二孩生育率在 2017 年达到 24.36‰,这也是带动生育率整体上 升的最主要原因,此后二孩生育率较 2017 年有所下滑,但整体来看,依然维持了自 2011 年以来持续 上升的趋势。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整体依然偏低,但自 2016 年以来也在不断上升。

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也分化:2015 年及之后生育率上升,与生育主力年龄段的变化并存。从政策变化 前后的平均生育率来看,2015 年-2019 年间,平均生育率达到 40.19‰,高于 2010 年-2014 年间的平均 水平 34.39‰。但分年龄段看,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平均水平变化情况差异较大,其中生育 率上升幅度较大的分别为 30-34 岁、35-39 岁、以及 25-29 岁年龄段育龄妇女,但 20-24 岁年龄段的育 龄妇女平均生育率是整体下降的。
2015 年之后虽然生育率上升,但育龄妇女人数快速下降,导致新生儿人数下降较快。根据抽样统计 人数显示,2019 年我国 15-49 岁育龄妇女人数较 2011 年下降了 18.4%,下降的主要是生育率高的年轻 育龄妇女,比如 20-24 岁育龄妇女人数下降了 44.4%,这与我国人口结构相关,考虑到 15-19 岁育龄妇 女人数降幅为 34.0%,高生育率的年轻育龄妇女人数下降对新生儿人数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从新生 儿人数看,生育政策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二孩和三孩的生育人数,2017 年起,二孩出生人数已经超过 一孩,成为新生儿主力,因此如果要稳定我国新生儿数量,政策应该重点从稳定或提高生育率入手。

一孩生育时间推后,生育率下降
25-34 岁育龄妇女成为一孩生育主要群体。从一孩出生人数占比结构看,2010 年-2014 年间,20-24 岁 育龄妇女的平均一孩出生人数占比达到 45.2%,明显高于 25-29 岁育龄妇女的平均一孩出生人数占比 33.2%和 30-34 岁的 10.7%,但在 2015-2019 年间,20-24 岁育龄妇女的平均一孩出生人数占比快速下滑 至 32.2%,一孩生育人数占比被 25-29 岁育龄妇女反超,后者快速上升至 43.0%,同时 30-34 岁的一孩 出生人数占比也上升至 12.9%。2015 年之后 20-24 岁育龄妇女不再是一孩生育的主要群体,如果从年 度一孩出生人数占比看,2015-2019 年间,20-24 岁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占比从 33.1%下降至 28.9%,反 观 24-29 岁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占比从 42.7%升至 44.8%,30-34 岁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占比从 12.4%升 至 17.0%。
2015 年之后,一孩生育率普遍较 2014 年之前下降。2015 年之后的两次生育政策改革没有改变一孩生 育率下降的趋势,整体来看,2015 年-2019 年间,一孩平均生育率 18.4‰,较 2010-2014 年间下降了 3.3‰。分年龄段看,2010 年-2014 年间,一孩生育率最高的 20-24 岁和 25-29 岁育龄妇女群体,在 2015 年-2019 年间,一孩生育率分别下降了 14.3‰和 8.5‰,并且 25-29 岁育龄妇女的一孩生育率已经反超 20-24 岁群体,成为一孩生育率最高的群体。另一方面,比较前后两个时间段,一孩生育率上升的分 别是 15-19 岁育龄妇女群体和 35 岁以上育龄妇女群体。我们认为一孩生育率在十年间的上述变化, 说明育龄妇女的生育时间普遍较此前有所推后。

二孩生育率意外的高
25-39 岁育龄妇女生育的二孩占比明显上升。二孩出生人数占比中,20-24 岁原本也不是主要人群,随 着生育年龄推后,2015 年-2019 年 20-24 岁育龄妇女生育的二孩人数占比进一步下降。近十年来,二 孩生育率最高的群体一直是 25-34 岁育龄妇女群体,在 2015 年之后随着两次生育政策放松,25-39 岁 育龄妇女人群的二孩生育人数整体占比从前五年的 78.3%进一步上升至近五年的 83.2%。
受生育政策放松带动,二孩生育率普遍上升。2010-2014 年二孩生育率平均水平为 11.1‰,近五年在 政策放松带动下上升至 20.3‰,说明政策对二孩生育率的正面影响较大,并且从各年龄段育龄妇女 的二孩生育率看,都出现了明显上升,特别是 24-29 岁和 30-34 岁育龄妇女,近五年相较此前二孩生 育率分别提高了 17.6‰和 17.7‰,说明生育政策放松应该尽早,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会更大。(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三孩及以上生育意愿更加超预期
三孩生育结构则前移到 20-34 岁育龄妇女人群。在三孩及以上出生人数结构中,25-34 岁育龄妇女是 主要群体的客观现实没有变化,并且在近五年得到进一步加强。2015 年-2019 年三孩及以上生育人数 占比,从此前五年的 59.4%上升至 65.9%,特别是 25-29 岁育龄妇女生育三孩人数占比较之前五年上 升了 4.76 个百分点。
39 岁以下育龄妇女的三孩及以上生育率大幅上升。虽然我国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低,但从近十年三孩 生育率的变化看却是持续且明显上升的,2010 年-2014 年我国三孩生育率仅为 1.8‰,到 2015 年-2019 年间,三孩及以上生育率已经提高到 3.1‰。以年为单位来看,2017-2019 年间,三孩及以上生育率逐 年提高 1.4‰、0.7‰和 0.6‰,明显高于 2015 年之前三孩及以上生育率的年变化幅度。分年龄段来看, 三孩生育率提高的情况也比较普遍,20-24 岁、25-29 岁、30-34 岁、35-39 岁之间的育龄妇女群体三孩 生育率在近五年相较前五年,分别提升了 1.4‰、2.6‰、2.5‰和 1.5‰。我们认为随着居民收入的逐 年提高,生育需求出现上升趋势。

对生育率低的误解:关注生育意愿的分化
生育政策放松明显带动了 2015 年之后二孩和三孩的生育率上升,但一孩的生育率却在下降。在生育 政策放松的背景下,2015 年-2019 年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明显较之前五年走高,说明我国的生 育率在下行大趋势之下有可能出现阶段性企稳甚至回升。但通过分析不同孩次出生结构和育龄妇女 生育情况对比之后,应该关注生育意愿出现的明显分化。
分化之一: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分化。从不同年龄段来看,20-24 岁育龄妇女此前是生育的 主要群体,但从近五年情况看,生育的主要群体年龄有后移的趋势:其中一孩的生育主要群体变为 25-29 岁育龄妇女,30-34 岁育龄妇女的二孩出生人数占比上升幅度最大,同时这两个年龄段的育龄妇 女在生育率和出生人数占比两方面都在逐渐成为我国新生儿孕育的主要群体。总的来看,育龄妇女 主要群体整体呈现出从 25 岁前后向 30 岁前后演化的趋势。
分化之二:20-24 岁育龄妇女内部的分化。从各孩次出生人数占比和生育率变化情况来看,20-24 岁这 一过去主要生育群体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一孩的出生人数占比和生育率均大幅下降,二孩生育率 上升但出生人数占比下降,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上升同时出生人数占比基本持平。结合 20-24 岁育龄 妇女生育率逐年变化趋势来看,20-24 岁育龄妇女人群内部分化主要包括两类情况:一类是一孩生育 率大幅下降反映出生育时间后移的群体,另一类则是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不断上升的群体。
如果要扭转我国新生儿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应该从生育率最高的人群需求入手,分析并解决 20-24 岁人群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同时为其中二孩及以上生育率上升群体,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

2 择偶:时间约束
20-24 岁人群面临的择偶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受教育时间增加延后了结婚时间,城镇乡村人口性别分 布不均增加了择偶成本,工作时间延长对生活时间构成挤出,网络普及率上升丰富了休闲方式降低 了择偶需求等。从结果看,就是婚姻登记时间向 25-29 岁后移。
受教育时间延长推后了一孩生育时间
与十年前相比,2020 年 20-24 岁人群的受教育时间更长。2010 年全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9.08 年,到 2020 年受教育时长已经上升至 9.91 年。细化到 20-24 岁人群当中,结构变化更明显。 2010 年人口六普数据中,20-24 岁人口的教育程度占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其 中男性初中受教育程度占比 46.1%,女性初中受教育程度占比 47.0%,远高于仅次的男性高中 22.2% 和女性高中 19.2%。2020 年时,20-24 岁人群中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已经相 对平均,男性大专学历占比 23.3%,本科占比 22.2%,女性大专学历占比 26.1%,本科占比 28.6%。从 受教育时长来看,相较 2010 年,20-24 岁人口当中,有更多人群处于学校在读状态,因此直接推后了 结婚和生育时间。

性别比不均衡增加择偶的难度
20-24 岁人口性别比普遍偏高,且在城市、镇、乡村之间分布不均。2020 年我国 20-24 岁人口中,男 性超过 3900 万人,女性超过 3500 万人,性别比达到 112.5,男女性别比明显偏高。从分布上看,城 市性别比为 107.0,镇性别比为 112.5,乡村性别比达到 123.1。首先,性别比偏高增加了择偶的难度, 其次城市、镇、乡村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适婚人口的错配。
15 岁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更高,且在各省之间差异较大。性别比偏高的情况不仅存在于 20-24 岁人群,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广泛存在。从 2019 年 15 岁以上未婚人口性别比情况来看,各省的平均性别比达 到 151.4,其中最低的西藏为 120.7,最高的天津达到 200,东北三省和西南五省的平均性别比最低, 分别为 141.2 和 142.1,华东地区最高,达到 155.8。

从低龄人口性别比变化情况看,择偶性别不均衡的问题仍将持续。从全国范围内 15 岁及以上未婚人 口性别比变化来看,2010 年之前基本维持在 140 下方波动,但 2011 年之后则出现持续上行趋势;20-24 岁人口性别比上升的趋势与此一致,2003 年-2009 年之间维持在 100 下方,当时造成社会广泛关注的 “剩女”现象,但 2010 年之后则持续上升,2019 年达到 2003 年以来的最高点 114.6。性别比不均衡 的情况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从 0-4 岁人口性别比看,均衡水平应该在 104-107 之间,但 2003 年以来, 我国新生儿性别比一直在 110 以上,因此性别比不均衡的问题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对 20-24 岁人口的婚育持续构成影响。
择偶的时间成本明显增加
城镇就业人员对“加班”的预期比较普遍。以城镇为例,20-24 岁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在 2019 年为 46.3 小时/周,从每周工作时间来看,是 2010 年以来第二短的年份。但从 2019 年城镇各年龄段 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来看,从 20-24 岁到 45-49 岁,城镇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整体呈现上升 趋势,期间工作时间唯一下降的就是 35-39 岁年龄段。20-24 岁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长较其他年 龄段明显短,或是主要受到工作经验约束,随着劳动熟练度上升,就业人员对工作时长增加的预期 也比较普遍。
网络普及改变了居民生活方式。除了工作时间变长之外,网络普及导致休闲方式发生明显变化,也 成为年轻育龄群体择偶意愿下降的原因。2010 年以来,我国网民每周上网时间逐年上升,特别是在 4G 技术商用之后,网民每周上网时间从 20 个小时下方跃升至 25 小时上方,随着应用场景日趋丰富, 2019年我国网民每周上网时间一度升至 30小时上方。从使用率变化看,网络视频和网络直播成为 2019 年以来上升最快的上网场景。网络普及化率不断提高,以及网络场景不断丰富,较大程度上改变了 年轻育龄群体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友需求,从时间和门槛两方面对择偶市场造成了明 显挤出。

婚姻登记年龄后移
从结果上看,就是适婚人群结婚年龄后移。2005 年我国 20-24 岁人群是婚姻登记人数的主要群体,在 当年婚姻登记人群中占比接近 50%,在教育时间延长、人口性别分布不均衡以及工作和上网时间挤 出等因素影响下,在 2013 年 25-29 岁人群的婚姻登记人数比例已经反超 20-24 岁人群,成为婚姻登记 的主要人群。截至 2019 年,晚婚的趋势仍在延续,20-24 岁人群婚姻登记占比已经下滑至 19.7%,与 此同时,30-34 岁人群婚姻登记占比自 2016 年以来持续大幅上升,已经达到 17.7%的历史最高水平。
3 生育:金钱约束
城镇化率上升的过程伴随着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的过程。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居民生活成本上升, 另一方面生育相关消费品的价格走势相较其他消费品更强,都对生育率有明显抑制作用。
城镇化率提升伴随着家庭户规模减小
近十年我国城镇化率与平均家庭户规模变化呈反向关系。2000 年之后,我国城镇化进度明显加快, 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城镇化率提升迎来最快速度,上升 13.9 个百分点达到 63.9%。在城镇化率提升 的过程中,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则出现明显下降。从全国来看,2010 年到 2020 年十年间,城镇化率 每提升 10 个百分点,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 0.3378 人。但从不同地区来看,城镇化率提升对家庭户规 模的影响差异较大: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如北京、西藏、天津、广东,城镇化率每提升 10 个百分点 分别对应家庭户规模减小 0.8805 人、0.7963 人、0.7767 人和 0.7152 人。

家庭户规模下降的趋势在城、镇、乡中是普遍存在的。从十年前后的家庭户人均户口对比来看,2010 年城市的家庭户均人口为 2.71 人/户,镇的家庭户均人口为 3.08 人/户,乡村的家庭户均人口为 3.34 人/户,基本符合家庭户均人口乡村最高,镇次之,城市最低的规律。到 2020 年,随着城镇化率从 50%升至 63.9%,城镇乡的家庭户均人口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城市降至 2.49 人/户,镇的家庭户 均人口降至 2.71 人/户,乡村降至 2.7 人/户。此时城市的家庭户均人口依然最低,但镇和乡村的家庭 户均人口数已经基本相当。
从各省情况看,城镇化率和家庭规模也呈反向关系。从 2020 年各省的城镇化率和家庭户规模看,也 基本呈反向关系:城镇化率最低的西藏,家庭户规模为全国各省最高水平,达到 3.19 人/户,城镇化 率最高的上海,家庭户规模为 2.32 人/户,仅略高于黑龙江、辽宁和北京,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62 人/户。

城镇化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
城镇化提高了居民收入,同时也提高了生活成本。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2.65 万元, 2020 年已经提高至 4.38 万元,较 2013 年增加了 65.3%,其中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 万元上升至 2020 年的 2.64 万元,增长 59.0%。相较之下,虽然增速低于同时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依然明显高于 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其中工资性收入的 1.71 万元和 6974 元。城镇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支出也明显上升。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7 万元,较 2013 年的 1.85 万元增长 45.9%,同样明显高于同时期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 1.37 万 元。
与 2013 年相比,2020 年城镇居民消费中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占比明显上升。2020 年城镇居 民消费结构整体与 2013 年相比变化不大,占比最高的仍是食品烟酒,其次是居住和交通通信,从变 化趋势上看,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占比依然维持下降的趋势。消费结构中变化较大的是居住、交 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居住消费的占比较 2013 年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达到 25.8%,仍是 仅次于食品烟酒消费的第二大支出项,但与食品烟酒的消费占比差距已经从 2013 年的 6.9 个百分点 大幅缩窄到 3.4 个百分点;随着我国老龄化率上升,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也明显上升;交通通 信占比上升与我国汽车人均保有量上升有较明显的关系。此外,2020 年教育文化娱乐的占比较 2013 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影响。(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2020 年与 2013 年相比,消费支出中与生育相关的消费支出增速更快。比较 2020 年较 2013 年全国居 民人均现金消费的大类和细分类增速来看,大类当中增速最高的是医疗保健 87.4%,其次是交通通信 69.8%,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和服务、以及居住的消费增速相当,分别为 58.7%、55.4%和 53.6%。但 是在细分类当中,个人护理用品增速最高,达到 181.6%,其次是住房维修及管理 94.4%、交通 89.8% 和教育 78.2%,其中较多都与生育相关,如改善型消费需求的住和行,以及必须消费的日用品和教育。

最近五年消费增速高低的品类比较:服务型消费需求更强。考虑到 2020 年有新冠疫情冲击影响,逐 年看消费额的变化或更能体现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2016 年-2019 年间,消费增速较低的分类包括食 品、衣着、家用纺织品和家庭日用杂品,消费增速较高的则包括住房维修及管理、个人护理用品、 交通、教育、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从消费趋势看,服务型消费的增速在期间明显更高,而必须消 费类则增速较低。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居民消费整体呈现收缩特征,其中必须消费品则表现出 了较明显的消费刚性,服务型消费则表现出明显的消费弹性。虽然新冠疫情影响了 2020 年弹性消费 的增速,但我们认为随着疫情的影响逐渐消退,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仍会体现在消费的增速和结构上。
价格波动给居民消费带来额外的支出压力
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压力一部分来自必须消费品价格波动。从居民消费结构可以看出,食品烟酒和居 住目前是消费占比最高的两项。以食品烟酒为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猪肉价格波动,导致食品支出 对其他消费支出的挤出。2013 年以来,食品烟酒消费占比一直在 25%-30%之间,整体维持下降趋势, 从消费增量的结构看,食品烟酒在 2018 年之前,其消费增量占比也自 2014 年的 28.9%逐年下降至 16.8%,但 2019 年和 2020 年受到猪肉供求结构变化的明显影响,CPI 中食品价格同比增速脱离了此前 的波动中枢 2%,猛增至 10%上下,受食品价格上升影响(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19 年和 2020 年食品烟酒在消费增量总的占比分别升至 26.6%和 89.7%。以 2019 年增量消费结构变化为例,食 品烟酒消费占比上升 9.8 个百分点,明显对其他消费形成挤出,比较明显的是居住消费占比下降 11.3 个百分点,生活用品及服务占比下降 3.2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占比下降 2.6 个百分点,所有其他消费 中占比保持上升趋势的是教育文化娱乐和其他用品及服务,占比上升 7.7 个百分点和 0.7 个百分点。

价格压力同时存在于必须消费品和可选消费品两方面。从近五年 CPI 来看,整体增速维持在 2.5%上 下,其中作为必须消费品的食品价格波动幅度从-1.4%到 10.6%,波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受到猪肉价 格波动的影响,从 2019 年的数据看,食品价格波动会对居民的其他消费构成明显的增量挤出。从与 生育相关度较高的部分可选消费品和弹性消费品的价格变化看,大城市的住房压力明显偏高,其次 是家庭服务价格持续走高,此外教育、学杂托幼费、教育用品等教育相关的消费价格在 2016 年-2019 年中也保持了持续高于整体的涨幅,即便在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服务型价格整体表现疲弱的背景 下,上述教育相关消费价格涨幅依然明显高于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无论是必须消费品的价格波动, 还是可选消费品的价格上升,都给城镇居民消费带来明显的支出压力,从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4 养教:资源约束
教育程度的预期回报强化了居民对教育资源的消费和需求,比较明显的体现在 K-12 教育方面。但在 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净流入地区的普通高中入学率却普遍低于其他地区。教育资源的相对紧张对生 育率形成进一步压制。
教育预期回报的正向引导
居民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强化了教育支出需求。数据显示,2021 年应届生就业中,博士毕业 生的月工资收入平均 2.48 万元,硕士毕业生的月工资收入平均水平为 1.12 万元,本科毕业生和大专 毕业生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 6331 元和 5417 元,明显高于统计局数据显示的城镇居民人均月工资收入 2130 元。受教育程度越高,统计显示平均薪酬收入越高,强化了居民教育投入的需求。
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从近十年我国每十万人拥有的受教育程度人 口变化来看,2010 年我国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人口最多,其次是小学水平,二者占比共计约 65%。 2020 年时,初中和小学仍是占比最高的受教育程度群体,但二者占比已经下滑至 59%,上升最为明 显的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从 2010 年的每十万人中不足 1 万人,上升到 2020 年的每十万人中超过 1.5 万人。

教育需求旺盛
教育消费支出持续走高。从居民消费中可以看出,2020 年以前教育消费的占比和增速持续双增。从 消费占比看,2014 年教育在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占比 4.61%,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持续上升, 在 2019 年达到 5.82%;从消费增速看,2014 年教育消费同比增长 5.26%,2015 年教育消费的增速已经 跃升至 11.42%,此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9 年更是达到 19.04%。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 教学机构以及教育消费方式出现较大变化,导致教育消费占比大幅回落至 3.67%,同时增速也转为同 比下降 12.1%。可以看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教育消费需求整体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教育消费明显集中在 K-12教育领域。以上市公司新东方在线披露的经营数据为例,2019年上半年-2021 年上半年期间,教育消费群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三类教育消费群体内部分化明显,与学前教 育消费群体人数断崖式下降,以及大学教育群体整体呈现平稳波动趋势不同的是,K-12 教育消费人 次从统计之初的 57 万人次迅速上升到了 2021 年上半年的 331 万人次。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教育消费群 体需求集中在 K-12 教育领域。

教育资源约束
普通高中入学压力加大。计算“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普通初中在校生人数”作为普通高中入学率的 参考,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自 2004 年以来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2004 年全国普通高中入学率 仅有 34.3%,上升的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5 年,达到 55.1%的最高点,此后开始下降过程,2020 年普通 高中入学率回落到 50.8%。从各地区 2020 年普通高中入学率横向比较看,最高的省份是吉林为 68.8%, 最低的省份是上海,仅有 35.6%,从地区来看,东北地区普通高中入学率最高,平均达到 64.1%,东 部地区最低,平均仅有 46.3%。
普通高中入学率下降的两种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或有两个。一是城镇化率提升导致的人口净流 动,对不同地区的学龄人数产生趋势性影响,但本地教育资源的供给量总体有限,因此在九年制义 务教育之外,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变得相对匮乏。二是在部分发达地区,教育体系供给结构多元化, 高中阶段的海外教育、私立教育可能不在“普通高中”统计范围内,因此导致普通高中入学率相对 偏低。我们认为后者对我国教育人口红利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主要是前者的负面影响较大。
省内二线城市普通高中入学率普遍低于本省平均水平。从 2020 年全国范围内部分省会或省内重要城 市与全省的普通高中入学率对比看,普遍存在低于全省的情况。从 13 个有数据的地区对比来看,省 会或省内重点城市普通高中入学率明显低于全省水平的包括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明 显高于全省水平的包括安徽、湖南、海南、宁夏,二者相对平衡的是山西、浙江、河南、贵州。整 体来看,省会或省内重点城市普通高中入学率偏低的省份,存在人口外流或人均 GDP 较高等特点, 省会或省内重点城市普通高中入学率偏高的省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均 GDP 偏低的现象。普通高中 教育是提高我国教育人口红利的起点,普通高中入学率下降,且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不仅意 味着存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而且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过程中,将造成城镇学龄人口教育红利 浪费。

5 关注 15-19 岁人口群体
15-19 岁人口的分化更加明显。一方面性别比开始达到极值,但整体来看生育率持续上行,另一方面 未上过学的人数和比例都较此前十年明显上升。未来十年之内我国将进入年轻育龄妇女群体稳定增 长时期,把握机会稳定生育率将成为扭转新生儿人数快速下降的关键。
生育率呈现上升趋势
一孩、二孩生育率都持续上升。首先作为前提要明确的是,我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 20 岁,但 15-19 岁育龄妇女是在统计范围之内的,基于此才会体现在人口普查数据当中。15-19 岁育龄妇女群体的生 育率虽然低,但从时间上看,2002 年以来却是持续上升的,截至 2019 年,15-19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达到 12.64‰,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一孩生育率 10.33‰,二孩生育率 2.21‰,都是历史最高水平。
生育率与育龄妇女群体趋势不同背后的关注点。随着医疗水平进步、教育水平上升、以及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幅上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总 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考虑到我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是 20 岁,以及 15-19 岁年龄对应的一般 教育阶段是高中前后,因此需要详细分析这一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上升背后的原因。

七普数据中 15-19 岁人口
性别比达到极值。从性别比来看,公认的相对均衡的出生性别比是 104-107,但从 2020 年七普数据来 看,我国 25-29 岁以下各年龄段都已经超出这一比例,其中 15-19 岁人口性别比达到 116.12,创下 2020 年我国各年龄段性别比的历史极值,并且显著高于 20-24 岁年龄段的 112.51。性别比偏高会显著提升 适龄人群的择偶困难,10-14 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较 15-19 岁有所回落,整体也高达 115.03,随着年 龄下降性别比逐渐回落,但 0-4 岁年龄段人群的性别比仍有 110.98,意味着男女不均衡的问题在未来 将持续一段时间。从城乡分布的角度看,性别比更加不均衡,其中 2020 年乡村的 15-19 岁人口性别 比达到 126.24。
城乡分布不均衡。2020 年 15-19 岁人群当中,44.9%的人生活在城市,28.2%的人生活在镇,26.8%的人 生活在乡村,但分性别看,生活在城市的男性占比 44.2%,低于女性的 45.8%,同时生活在乡村的男 性占比 27.9%,显著高于女性的 25.6%。由此导致城镇中 15-19 岁男性较女性多出 316 万人,而农村中 男性较女性多出 226 万人。性别分布不均衡实际上不利于生育率提升,与 15-19 岁育龄妇女生育率上 升的趋势是相悖的,或说明育龄妇女人群内部出现分化,部分女性生育时间有所提前。

2020 年 15-19 岁人口受教育情况
未上过学的人数和占比明显较此前增加。虽然我国整体国民受教育时间上升,但自普及九年制义务 教育之后,不同年龄段的受教育情况再次出现分化。根据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20-24 岁年龄段较 25-29 岁年龄段,未上过学的人数是下降的,但自 15-19 岁人群开始,未上过学的人数有所回升,并且 10-14 岁未上过学的人数较 15-19 岁大幅增加。未上过学人数上升的情况,在男性中表现的更加明显。考虑 到我国新生儿人数和性别比的波动情况,从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来看,15-19 岁年龄段人口中,0.48% 未上过学,明显高于 20-24 岁年龄段的 0.36%和 25-29 岁年龄段的 0.38%,而 15-19 岁年龄段中男性未 上过学的占比 0.48%要略高于女性的 0.47%。另一方面,10-14 岁应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口中,1.3% 的人未上过学,包括男性中占比 1.27%,女性中占比 1.33%,较其他年龄段大幅抬升,更值得关注和 警惕。
新生儿变化与人口问题的转机
解决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问题,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改革,既要尊重和保护有生育意愿的 育龄妇女,又要坚持九年制义务教育贯彻落实,维持住我国教育人口红利优势。
2000 年-2017 年间是新生儿总人数基本平稳阶段。新生儿人数取决于育龄妇女人数与生育率的水平。 从生育率最高的人群 20 岁以上人数来看,受益于 2000 年之后出生人数结束了此前超过十年的下降阶 段,进入约十五年的持平阶段,在七普数据发布之后,我国即将进入出生人数平稳期,在此期间育 龄妇女人数快速下降的问题得到阶段性解决,这是稳定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新生儿人数的大前提。在 生育率方面,目前 15-19 岁育龄妇女人群已经出现生育率整体持续上升的趋势,如果政策能够针对适 龄群体的择偶、生育和养教相关问题提供帮助,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将事半功倍。
未来 5-10 年需要重点关注乡村学龄人口教育情况。在关注新生儿人数的同时,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教育人口红利。从七普数据中,已经出现学龄人口未上过学人数和占比大 幅上升的情况,从低龄人口的分布来看,目前 15-19 岁人群在城市的占比为 44.9%,乡村的占比仅为 26.8%,但在 10-14 岁人群当中乡村的人数占比跃升至 41.6%,这可能是该年龄段未上过学人数占比大 幅上升的重要原因。并且 10 岁以下的人口结构中,乡村人口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整体来看,我国未来仍需加大乡村教育落实力度。

6 结论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在 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 年 5 月,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受生育政策放开影响,我国 生育率在 2017 年之后整体明显上升,但由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出生人数自 2016 年之后持续大幅下 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出生人数既与育龄妇女人数和结构相关,又与生育率相关。育龄妇女中生育率最高的一般是 20-24 岁群体,但我国生育政策改革后,20-24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整体是下降的,生育率上升幅度较大的 分别为 30-34 岁、35-39 岁、以及 25-29 岁年龄段育龄妇女。
分孩次来看,一孩的生育时间推后且生育率下降,25-34 岁育龄妇女成为一孩生育的主要群体;二孩 的生育率在生育政策改革之后明显上升,25-39 岁育龄妇女生育的二孩占比明显上升;三孩及以上孩 次的生育意愿更加超预期,并且生育结构意外前移到 20-34 岁育龄妇女人群。
因此对我国的低生育率,应该从分化的角度来看。分化之一: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分化, 育龄妇女主要群体整体呈现出从 25 岁前后向 30 岁前后演化的趋势。分化之二:20-24 岁育龄妇女内 部的分化,一类是一孩生育率大幅下降反映出生育时间后移的群体,另一类则是二孩和三孩及以上 生育率不断上升的群体。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适龄人群面临诸多约束。
择偶的时间约束。截至 2020 年,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延长到 9.91 年,相较十年前, 20-24 岁人群有更大的比例处于学校在读状态,因此直接推后了结婚和生育时间。其次是男女分布不 均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性别比明显偏高,而且在城、镇、乡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再者是受工作时 间变化和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影响,适龄人群的择偶时间存在被其他事项构成时间挤出的情况。从 结果来看,就是我国的婚姻登记年龄明显后移。
生育的金钱约束。城镇化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趋势,但从历史规律来看,城镇化率提升的过程也 是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的过程。并且城镇化虽然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也明显提高了均生活成本。 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看,2020 年城镇居民消费中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占比明显上升;从消 费增速看,增速较高的包括住房维修及管理、个人护理用品、交通、教育、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服 务型,消费需求更强,且较多与生育相关;从价格看,无论是必须消费品,比如食品,价格波动对 其他增量消费的挤出,还是可选消费品,如住房,受供需格局影响产生的价格持续上涨压力,都对 居民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更何况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教育、学杂托幼费、教育用品等价格在 2016 年-2019 年中也保持了持续高于整体的涨幅。(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养教的资源约束。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强化了居民的教育支出需求,教育需求旺盛,体现在 消费支出中占比持续走高,从消费方向上看则明显集中在 K-12 教育领域。但我国的教育资源存在约 束,普通高中的入学压力自 2015 年逐年加大,并且在不同省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分化:人口净流入 程度,以及人均 GDP 发展程度,是造成普通高中入学率分化的两个重要因素。普通高中的入学压力 上升,强化了居民教育消费的预期,进而进一步抑制了生育率。
但我国的新生儿逐年下降的问题也有转机。一是 2000 年之后我国出生人口结束了此前持续下降的趋 势,并在此后大约 15 年期间,出生人口维持平稳,这意味着育龄妇女的人数基本能够维持稳定。二 是七普数据中 15-19 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较此前出现持续明显上升的趋势,一定程度上表明育龄妇女 的生育意愿分化有扭转的可能,接下来的生育政策改革措施在落实的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取得成效。 但另一方面则需要关注的是,我国要坚持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教育人口红利,但七普数 据中的学龄人口明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 10-19 岁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大幅攀升,二是 14 岁以下人 口在乡村的占比大幅上升。二者共同指向了乡村的九年义务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精选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

已有位网友浏览此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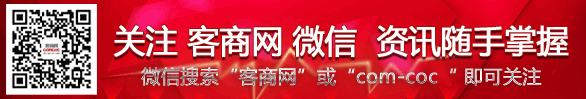
 中国经济必将破浪前行
中国经济必将破浪前行 进一步激发境外旅客入境旅游消费活力离
进一步激发境外旅客入境旅游消费活力离 商务部:创新优化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 促
商务部:创新优化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 促 新兴产业“抢人” 现代服务业“吸才”—
新兴产业“抢人” 现代服务业“吸才”— 2025全国民营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
2025全国民营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 河南发文支持就业!归集重点产业企业用
河南发文支持就业!归集重点产业企业用 同比增长5.3%!
同比增长5.3%!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第二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第二 “调研不是走过场,是沉下去、扎进去”
“调研不是走过场,是沉下去、扎进去” 圣境甘南:从草原到山城的县域振兴实践
圣境甘南:从草原到山城的县域振兴实践 盐都富顺 梦里水乡
盐都富顺 梦里水乡 “一针一线”织就创新引领的担当和勇气
“一针一线”织就创新引领的担当和勇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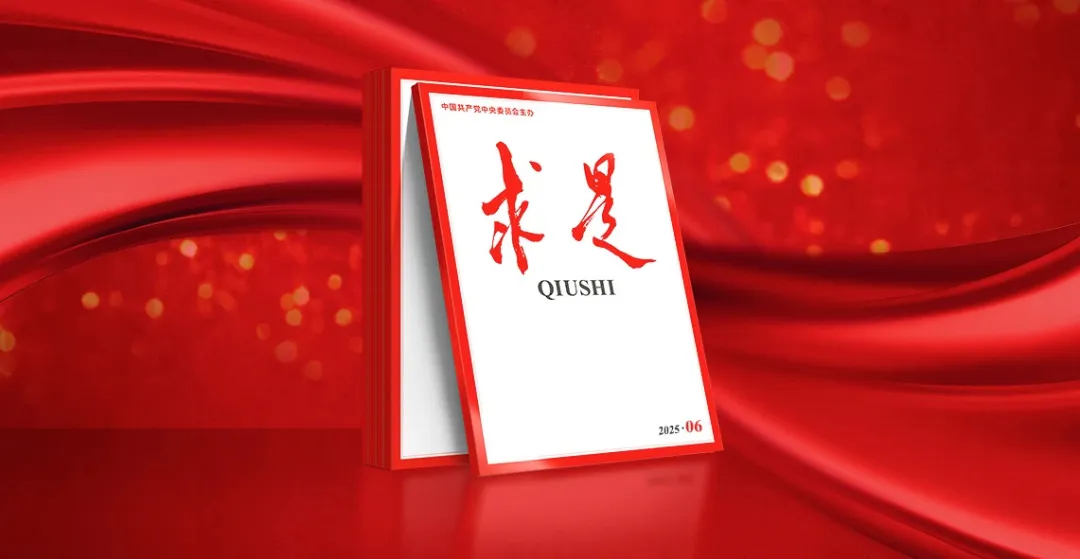 《求是》杂志刊发中共全国工商联党组署
《求是》杂志刊发中共全国工商联党组署 两会聚焦|争做创新主体,构筑竞争优势
两会聚焦|争做创新主体,构筑竞争优势 沈莹出席广东省民营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
沈莹出席广东省民营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 全国工商联与中国建设银行召开2025年推
全国工商联与中国建设银行召开2025年推 天山明珠耀丝路 哈密逐梦谱新篇
天山明珠耀丝路 哈密逐梦谱新篇 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管理改革工作会议
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管理改革工作会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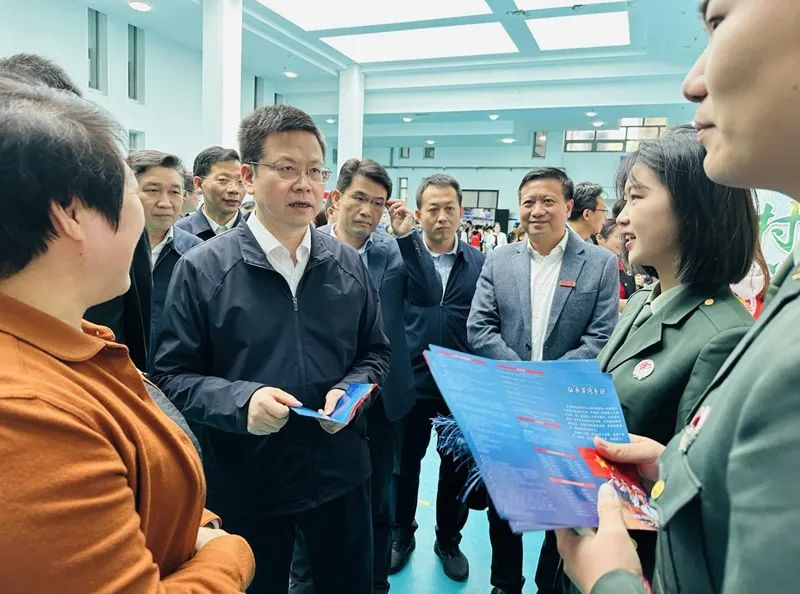 2023“百城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
2023“百城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支部赴李大钊故居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支部赴李大钊故居